导语: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将蔚来及CEO李斌、前CFO奉玮告上美国法院,指控其通过与宁德时代等合作成立的武汉蔚能电池资产公司虚增收入。
10月16日,蔚来港股盘中暴跌超13%。
导火索来自一纸起诉书——全球第六大主权财富基金、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在今年8月正式将蔚来汽车及其CEO李斌、前CFO奉玮告上美国法院,指控其通过与宁德时代等合作成立的武汉蔚能电池资产公司(Mirattery),虚增收入、误导投资者。
这是史上首例国家级主权基金起诉中概股的案件,也让蔚来的“换电故事”陷入新的信任危机。
01 蔚能与BaaS,“创新”还是“财技”?
蔚来(9866.HK)股价在消息传出后遭遇重挫,盘中跌幅一度超过13%,创下今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截至10月16日收盘,蔚来港股股价下跌8.99%,收盘价为49.28港元/股,总市值1219亿港元。
消息的源头,是财新网10月15日披露的独家报道:GIC 已于 2025 年 8 月在美国新泽西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蔚来通过关联交易虚增收入并隐瞒对蔚能的控制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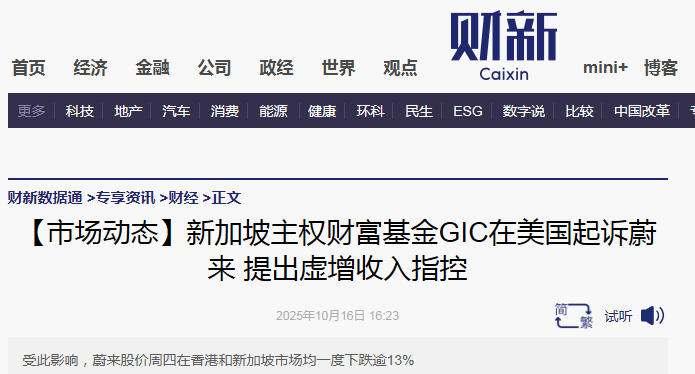
图源:财新网
GIC 在起诉书中称,蔚来在2020年通过与宁德时代等合作伙伴共同设立的武汉蔚能电池资产公司(Mirattery),人为制造了业绩增长的假象,从而推高股价,导致其投资蒙受损失。
这是全球主权财富基金首次以原告身份单独起诉中概股企业。
这起诉讼的特殊性远超案件本身:
主权财富基金,通常是国际资本市场上最为稳健、最不喜欢“抛头露面”的机构。当连这样一类资金都选择走上法律途径,意味着一场关于跨境信任与治理体系的深层裂变,已经开始。
诉讼的核心聚焦在蔚来2020年推出的“电池即服务”计划。该模式将“车”与“电池”剥离,车主只需购买车身,电池由独立公司蔚能统一持有并租赁给用户。蔚来因此获得稳定租金收入,看似是创新的资产轻量化尝试。
然而,GIC在诉状中认为,蔚来在与蔚能交易时,并未采用分期确认租赁收入的方式,而是选择在电池出售当下将全部金额计入营收。这一做法令公司业绩在短期内出现了异常增长,从而可能误导投资者对经营状况的判断。
举例来说,用户订了个BaaS服务,要分5年交租金,根据美国会计准则(ASC 606),此类收入应随着用户按月支付租金逐步确认。但蔚来一次性、提前把这5年的钱全部入账了。

公开财报显示,蔚能正式运营后的第一个季度,蔚来营收便从前一季度的不足30亿元跃升至逾66亿元,同比增长超过一倍。GIC据此指出,若收入按照长期租赁逻辑分期入账,蔚来的增长曲线不会如此陡峭。
该基金在文件中指出,这种提前确认收入的做法让公司的盈利表现“被人为放大”,投资者因此难以准确评估其真实经营动能。
若按GIC认为合规的分期确认方式处理,蔚来2020年第四季度收入同比翻倍的财务表现将被大幅削弱。
蔚来的说法则截然不同。
蔚来坚持认为,电池出售时控制权已完全转移,“履约义务”已完成,因此一次性确认收入符合《美国会计准则(ASC 606)》的要求。蔚来还强调,审计师普华永道在审计中并未提出异议,且所有交易均在财报中披露为关联方交易。
但GIC并不认同。
他们认为蔚来与蔚能之间的关系“远超普通商业合作”,关键问题在于:蔚能是否被蔚来“实质控制”。
02 控制权迷雾:蔚能是“合作公司”,还是“马甲公司”?
在蔚来财报中,蔚能的股权结构清晰:蔚来持股19.84%,宁德时代、国泰君安、湖北科技投资等为其他股东。
但GIC认为,这个持股比例“恰好卡在20%以下”,是刻意规避合并报表的门槛。
GIC列举了三项核心证据:
1. 股权设计的“巧合”:19.84%的持股比例并非偶然,而是为避免触发美国会计准则中“潜在控制权”审查而刻意设定的界限。
2. 经济利益的“隐藏控制”:虽然表面持股不足20%,但蔚来通过应收账款担保、租赁付款回购等方式,在蔚能中实际享有约55%的经济利益。
3. 业务依附的“实质控制”,蔚能100%的业务依赖蔚来:比如电池采购由蔚来决定;租金价格、种类、数量由蔚来制定;电池维护与用户租赁流程也由蔚来负责。
在GIC看来,蔚能完全无法独立运营,是蔚来的“财务延伸体”,应被认定为可变利益实体(VIE)。
若这一判断成立,蔚来必须将蔚能的财务数据纳入合并报表,意味着过去确认的数十亿元收入都将被“冲回”,并可能构成信息披露不实。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证监会(SEC)曾在2022年9月就蔚能交易向蔚来发出问询信,要求解释收入确认和控制关系。蔚来当时回应称“一切符合会计准则”,SEC未采取进一步行动,但并未明确背书。
03 GIC的“后发制人”GIC 的出手并非意气用事。
在国际金融圈,这家成立于1981年的主权财富基金,一直以“沉默的资本巨鳄”著称。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的设立,起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彼时,新加坡经济快速发展,外汇储备规模迅速扩大,政府决心将闲置资金交由专业机构管理,以应对全球通胀与资本波动。
1981年,GIC正式成立,成为全球最早的主权财富管理机构之一。根据其最新年度报告,GIC目前的资产管理规模接近8,000亿美元,投资遍布全球约40个市场,长期回报率保持在5%至6%之间。
根据其《2023/24年投资报告》,过去20年平均年化名义回报率为5.8%,实际回报率3.9%。
GIC坚持“长期主义”,强调“在可接受风险下实现超越全球通胀的回报”。
与新加坡的另一主权基金——淡马锡控股不同,GIC不直接持股具体企业,而是专注于全球资产配置,包括股票、债券、房地产、私募股权、基础设施等。
在蔚来前期发展过程中,GIC 与淡马锡、红杉资本、高瓴资本等并列,均是蔚来的知名机构投资方之一
除了投资,实际上,GIC其实还是一位“诉讼老手”。
早在2014年,GIC就曾因BP漏油事件中的虚假披露起诉对方,并最终获得和解;2020年,又以信息披露失实起诉加拿大药企Valeant;2021年起诉Celgene涉嫌药品定价造假。
这些案件大多以和解收场,GIC在“维护主权资产”与“保持机构形象”之间拿捏得恰到好处。
此次起诉蔚来,被业内视为GIC“后发制人”的典型策略。
蔚来被灰熊做空报告指控的时间是2022年;GIC真正起诉却是在2025年8月。
分析人士指出,GIC在等待的是损失的“制度性确认”——蔚来股价自2021年高点62美元跌至今年不足10美元,跌幅超80%,账面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当损失规模构成“重大事件”,GIC不但有权利,更有义务采取法律行动,以证明其履行了受托责任。
据“观察者网”等媒体报道,GIC在2020年8月-2022年7月间,累计买入5445万股蔚来ADS,按股价波动估算损失可能达5亿-20亿美元。
04 蔚来的资本困局:融资神话与盈利幻象
从2018年登陆纽交所以来,蔚来始终被贴上“融资高手”的标签。
七年间,公司累计净亏损超过1200亿元人民币,是新势力车企中唯一尚未实现盈利的品牌。
但在资金链屡屡告急之际,蔚来总能“起死回生”:2019年,合肥对其注资70亿元,换得地方版“国资救援”;2023年:阿布扎比主权基金出手,提供约210亿元人民币战略投资;2025年9月,蔚来完成10亿美元股权增发。
截至今年上半年,蔚来账面现金仍超过500亿元。
然而,连续多年亏损和高额研发开支(长期占营收40%以上)令外界质疑:蔚来的盈利模式究竟何在?
在内部,李斌早已下达“死命令”——四季度必须盈利。
为此,蔚来实施了所谓“基本经营单元改革”,即拆分公司内部成本中心,每个单元独立核算利润。CFO曲玉在投资者会议上透露,随着新车型上量,公司四季度整车毛利率有望提升至17%。但这一切努力,可能因GIC的诉讼而蒙上阴影。
一旦诉讼进入实质阶段,不仅会影响蔚来与资本市场的关系,还可能影响其在阿布扎比、香港等地的未来融资能力。
蔚来曾是中国新能源叙事中最耀眼的符号之一。
从李斌的创业神话,到合肥救援、再到三地上市,蔚来代表了一代企业家的“科技信仰与资本冒险”。
但当故事被国际资本的起诉打断,信任成为最稀缺的资源。
蔚来能否走出这场风暴,取决的不仅是法院的判决,更取决于它是否能在资本规则的舞台上,重新赢得一个“透明的未来”。
最后值得探讨的是,GIC对蔚来这起诉讼的意义,早已超越蔚来本身,它至少在3个层面具备信号意义:
其一,是创新与会计准则的碰撞。
蔚来的BaaS模式是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商业创新,但在传统会计准则下,收入确认与资产转移的界线模糊。
GIC的起诉表明,国际机构投资者对“创新”背后的会计合规容忍度,正变得更低。
其二,主权基金的角色转变。
长期以来,主权基金被认为是“永不维权”的长期投资者。但GIC、挪威主权基金等近年来开始通过诉讼、股东提案等方式表达不满。
这意味着,国家资本正从被动股东变为主动治理者。
其三,对中概股信任体系的冲击。
在中美监管摩擦、会计监管趋严的背景下,GIC的诉讼可能成为新的“信号事件”。未来,国际机构或将要求中概股披露更详细的交易信息,甚至要求第三方会计师承担更大责任。
前有闻泰科技、今有蔚来事件,这些眼前的案例已经敲响警钟,在未来的国际市场博弈中,相关企业需要不仅要面对市场竞争,更要面对来自属地政策、制度上的冲击。

